罗尔夫·施蒂尔纳 周翠:当事人主导与法官权限-ag亚洲游戏国际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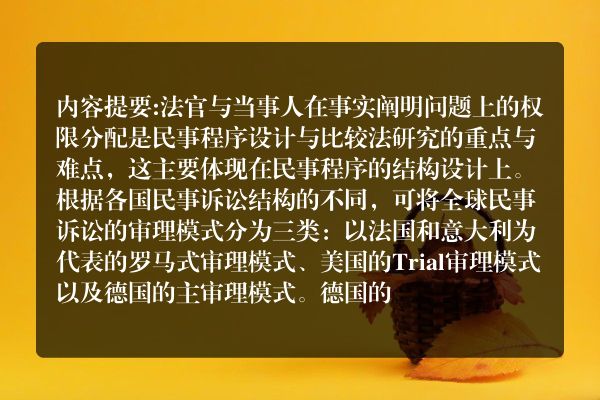
内容提要: 法官与当事人在事实阐明问题上的权限分配是民事程序设计与比较法研究的重点与难点,这主要体现在民事程序的结构设计上。根据各国民事诉讼结构的不同,可将全球民事诉讼的审理模式分为三类: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罗马式审理模式、美国的trial审理模式以及德国的主审理模式。德国的主审理模式很好地诠释了诉讼集中主义,并将“法官对诉讼进行实质指挥”与“在一个期日集中进行辩论与证据调查”结合在一起,从而具备了快捷、高效与高质的优点。这种模式在辩论主义的框架范围内凸显了法官的主动角色和法官在事实阐明问题上的协助责任;法官通过与当事人开诚布公的对话以及全面积极主动地行使实质指挥诉讼的义务,避免了突袭裁判,提高了判决的正确性以及程序效率,并最终促使诉讼尽可能在一个审级结束。从这一意义上看,德国民事程序并不像英美法系学者认为的那样具备“繁文缛节和等级森严”等特点,相反,德国民事诉讼作为自由与高效诉讼文化的产物已成为“对话诉讼”的典范,从而代表着现代诉讼的潮流。
关键词: 当事人主导,法官权限,辩论原则,主审理
前言
在庆祝卡尔·海因茨·施瓦布(karl heinz schwab)教授九十诞辰的学术交流会上,本题目{1}再次成为学术研讨的内容。虽然这一题目属于德国民事诉讼法学界长期探讨的课题{2},并不新颖,但新近再次对其进行研究,仍然具有意义。原因有二:其一,几乎所有诉讼文化下的诉讼法学家无不对这一基本问题进行过持续探讨{3}。卡尔·海因茨·施瓦布教授也尤其在罗森贝克(rosenberg)的教科书中对当事人权限和法官权限的基本分配进行过研究,并一贯主张两者之间应当适当协调{4}。其二,这一基本问题在欧洲和全球的比较法研究中仍一如既往地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国际诉讼法协会的最近一次大会上,虽然英美法系的学者在描述大陆法系诉讼的特征时不再使用“纠问”的字眼{5},但却使用了“繁文缛节和等级森严”(bureaucratic andhierarchical)的用词,明显影射与此相连的社会结构。与之相对,英美法律文化的代表人物将自身的诉讼模式与法官克制和公民自由联系在一起。在目前这个英美法系的法律和经济的统治地位尚未终结的时代,这种潜在的和公开的联想对于法律的进一步发展并非毫无意义,即使欧盟也常常以英美法律文化为导向,这种文化比欧洲人更早地开始将“市场自由”置于其发展的中心位置。在此背景下,放弃对臆想中认为不存争议的基本问题进行关注和探讨是不智的。欧盟不断地在诉讼法领域张开大胃口,逐渐从判决承认领域转向了内容调控,例如小额程序或反不正当竞争诉讼都已成为或即将成为欧盟二级立法的内容。下文的思考将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法官和当事人的权限进行探讨:诉讼结构和程序责任的分配;法院和当事人之间的对话;当事人对事实自治和依职权调查证据;当事人诉讼和民事司法的私人化。
一、诉讼结构和程序责任的分配
程序责任的分配尤其反映在诉讼结构上,其在各个法律文化中有不同的形态。今天,对西方文明中的诉讼结构,人们原则上可以分为如下三种基本结构:{6}带有意大利教会法印迹的罗马式诉讼模式、英美法系的trial审理模式、和由法官对主审理(hauptverhandlung)进行准备的现代模式。
(一)带有意大利教会法印迹的罗马式审理模式
这种审理模式直到今天还适用于法国{7}和意大利的诉讼{8},但不再适用于西班牙。在第一个书面阶段—起诉与答辩阶段,当事人陈述事实,法官进行严格的正当性审查。通过这种方式,法官即可及早对诉讼资料进行限定和引导。仅对存在争执的正当事实,才会在第二个阶段—所谓的指示阶段(instruktionsphase)—通过“审前准备法官”(juge de la mise en etat)或者“调查法官”(giudice d’ istruttore)收集证据,这或者依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进行。在事实阐明之后,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对事实收集的结果和重要的法律问题进行辩论并最终作成判决的阶段。这一诉讼模式的典型特点是:原则上,法官负责重要的法律;当事人负责事实,法官对此进行指挥,但他并非必须如此:“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交事实说明,如果他确信这对解决纠纷而言深有必要”(《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8条)。是否对诉讼实施实质指挥,基本属于法院裁量的范围。这意味着,法国或意大利的法官{9}可以但并非必须积极主动地塑造程序,实际上他们也常常并不这样做。特别是在指示阶段,程序常常由一系列的期日拼接而成,时间上的拖延并不少见。正是因为证据调查和作成判决的言词辩论之间互相分离,才造成了虽然法官在择取程序的法律基础和诉讼资料收集方面发挥了主动作用但整个程序仍然在许多方面缺乏效率的局面,因为当事人双方或至少一方可以利用分立的程序阻塞程序进程,所有的程序参与人都可以利用此点安逸而闲适地进行诉讼。因此,在这种诉讼文化中,例如特别是在法国,普通的民事程序让位于临时救济程序或者预决程序{10}的情形并不少见。在这些程序中,在权利“明确”的情形法官有时被赋予了很大的裁量空间,并因此在加重当事人的责任基础上加强了法官的权限。对这种通过消减权利保护的质量来加快诉讼的做法,卡尔·海因茨·施瓦布原则上持怀疑态度{11}。非常不幸的是,在对低于2000欧元债权—毕竟这一数目已相当于许多普通公民一个月的净收入—适用的《欧盟小额程序法令》{12}中,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
(二)trial审理模式
一如最初在所有的英美法系国家中所实施的那样{13},trial审理模式虽然也由书面的起诉与答辩程序开启—所谓的“诉答阶段”(pleading phase),但在此阶段并不会出现以让法官进行严格的正当性审查为目的的事实陈述。毋宁说,争讼资料在这一所谓的“告知诉答”(notice pleading)阶段只须被概括陈述即可。即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进行“事实诉答”( factpeading) {14},但这也很少涉及可以精确和详细涵摄的事实,而更多涉及充分的可信性说明。也即,必须让法官确信:诉是基本可信的,从而不会被法官一开始就驳回。因此归根结底,这里并不要求法官通过正当性审查(所谓的“严格的相关性审查”)在“将诉讼资料严格限缩为重要的事实”的意义上实施诉讼指挥。一旦法官确信案件是可信的,他将保持被动角色。在第二个阶段,所谓的“开示阶段”(discovery stage),双方当事人收集事实和证据手段,但这仅是为了自己知情,而非为了让法院获得信息,法院通常并不了解案件和案卷。直到第三个阶段—“trial”阶段,双方当事人才对事实进行汇总,并连同证据资料以言词方式向法院提交,法院仅在少数情况下并在狭窄的范围内进行阐明。附随事实和证据资料,原告确定了他所申请的权利救济的确切的法律基础。这种诉讼结构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法官角色的承担,法律仅在例外情形容许法官进行主动干预。此外,这一诉讼结构实质上根本既不承认也不准备承认事实陈述与证据提交在程序法上的严格区分。
(三)主审理模式
第三种模式是对传统罗马式诉讼模式和trial审理模式的新式结合。这体现在现代德国的诉讼{15}、西班牙最新的诉讼改革{16},以及现代改革后的英国诉讼的若干方面上{17}。与罗马式诉讼模式一致,此种模式的第一阶段—起诉与答辩阶段—也要求当事人进行严格的正当性事实陈述和争辩。法官不仅对这些陈述进行可信性审查,而且也进行严格的正当性审查,以便早期对诉讼资料进行引导,因此这种模式要求法官扮演主动的角色,并对整个诉讼进行实质指挥。此外,这种模式从trial审理模式中吸收了通过一次主审理( hauptverhandlung)进行证据调查和言词辩论的思想。中间的诉讼阶段(第二阶段)被塑造为准备阶段,并将“法官通过证据调查进行指示(晓谕)和阐明”的灵活要素与“当事人负责将事实和证据手段补充完整”的要素结合起来。此阶段既服务于法院知情,也以当事人之间交换信息为目的{18}。在主审理中,只有那些通过前置的信息交换和法官阐明未能充分澄清的主要争点,才成为证据调查和辩论的对象。由此,这一所谓的中间阶段结合了罗马和英美法系传统的优点,并在高质量、快速澄清事实的意义上保障了最佳效率。与德国和西班牙相对纯粹地贯彻了这一模式—这也被诉讼统计数字证实为卓有成效—相比,英国的诉讼却显得半心半意,因为它要求不同的法官实施案件管理(case management),却并没有赋予后面的裁判法官进行清楚的正当性审查的充分的可能性。这种集中的主审理程序的诉讼模式,在学理上深受支持。rosenberg/schwab教科书也对1976年简化附律所确立的德国模式大加赞赏{19}。此后,这种模式在国际示范法上也大获全胜。这不仅被确立在《拉丁美洲现代法典》(codigo modelo iberoamericano) {20}中,而且也被规定在《跨国民事诉讼程序原则》(principles oftransnational civil procedure)中。后者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和美国法学会(americanlaw institute)于2004年通过并于2006年公布{21}。如此一来,加强法官实质指挥诉讼同时又将辩论和证据调查集中于一个期日,就成为现代国际[民事诉讼法]的潮流所向。
二、对话诉讼作为自由和高效诉讼文化的产物
特别是法官实质指挥诉讼这一点,促使很多英美法系的诉讼法学者做出了“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民事诉讼具有繁文缛节和等级森严的特征”的判断。mirjan damaska {22}对诉讼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真正或臆想的关联所作的分析,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尝试。他在绝对极权的压力下离开了欧洲,并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找到了法学研究的新家园,并最终成为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新近,纽约大学法学院的oscar chase在其专著的一些章节中对这一基本思想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再思考{23}。目前来看无疑正确的是,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相比更强地部分与福利国家的组织形态联系在一起。这明显体现在普鲁士王国弗里德里希时代的诉讼{24}以及一百年之后受klein影响的奥地利民事诉讼中{25}。此外,认为社会主义的诉讼文化以主动法官和诉讼上的纠问主义为典型特征的说法,也同样正确{26}。但另一方面,并非完全自由的威廉二世时代的帝国民事诉讼却比现代德国民事诉讼呈现出更强的当事人诉讼的特点,这同样适用于过去二百年的罗马式诉讼规则,不论其社会如法国更加体现出民主的结构,还是如意大利和西班牙更加倾向于等级制甚至有时出现极权{27}。反过来,现代英国民事诉讼法向着法官实质指挥诉讼方向的转变{28},很难就得出现代英国社会具有等级化的特征。在当前这个现代世界里,将从超过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过去某特定时代得出的结论强制适用于目前的社会结构上,并不特别令人信服。再加上,任何现代的开放社会都会受到多种多样的全球化影响{29}。现代欧洲社会语境下的法官实质指挥诉讼,首先是一种诉讼方式,而非法官实施权限的形式。指挥诉讼是保证法定听审权的手段,并因此成为诉讼对话的工具。它是对话民事诉讼(dialogischer zivilprozess)的一种表现形式。{30}
借助于德国诉讼可以很容易地对此模式做出阐释。虽然如同gottwald在rosenberg/schwab教科书中所描述的一样{31}并不存在法官进行法律对话的普遍义务,
但是《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39条、第272条及其之后几条规定的法官指示义务和准备义务,导致法院应公布其在正当性审查及限制诉讼资料后形成的临时法律观点。通过这种方式,当事人不仅获悉了未来判决的法律范围,而且也避免了不必要的事实和证据探知。当事人对法院的法律观点发表意见,可以使法院对可能的误解和不确定性进行查证,从而提高了程序的效率。最后,依照第279条第三款、第285条对证据调查的结果进行探讨和辩论,至少可以使法院合乎逻辑地宣告即将做成的裁判的内容,同时当事人也有机会对此发表意见,这就避免了突袭和提高了正确性保障。如此一来,当事人和法院都被促使亮出底牌,以尽可能在一个审级就终结程序。这种对话诉讼在当事人和法院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工作共同体(arbeitsgemeinschaft)的形式—卡尔·海因茨·施瓦布参照罗森贝克的观点,很早就对这种方式的特征作出了如上描述{32}。这并不是过于理想化的和脱离现实的想象,而是对辩证的审判程序进行系统化的尝试,以在利用所有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尽可能理想的探讨{33} 。《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总则特别是第16条同样以对话模式为出发点{34},但其用词比《德国民事诉讼法典》更加清晰{35} 。
综上,法官对诉讼的实质指挥并不意味着他凌驾于双方当事人之上,相反他是对话伙伴。在对话中,积极活动和指挥被视为他的义务和责任。如今,更确切地说,法官和律师之间的等级形象其实更多地体现在传统的英美法系诉讼中。在这样的诉讼中,典型情形是:法官为了作出裁判会保持沉默{36}。维持这种在形式上理解的中立,其代价是昂贵的,因为对话的缺失导致了当事人的不必要的活动,可能出现的法官错误也不能在宣告裁判前被消除。
所谓的“繁文缛节”这一特征的确切含义,不甚明了。大陆法系的程序远不如英美法系那么拘泥于形式。这不仅指言词辩论程序—在德国,这更像一个公开的圆桌会谈,类似于“例行商务会议”{37},而且也指书状—比起大陆法系国家,许多英美法系诉讼文化对书状的形式要求要严格得多{38}。如果繁文缛节是指数量庞大的法官和法官职业生涯的话,那么尽管从单纯的外在形式上看这种对行政公职机构的譬喻倒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为了实现广泛的事实调查目的的审前程序以其庞大的律师军团所达到的机械的形式化程度,与独立自主进行探知的行政日常工作完全势均力敌。不仅存在官方组织的官僚主义形式,而且私机构的[官僚主义形式]常常不输于官方机构。语言上的障碍和对欧洲尤其是德国法律文化与政治崩溃的黑暗时代的记忆,常常导致对当下的诉讼现实进行选择性感知{39}。
此外,《跨国民事诉讼程序原则》—其由美国法学会通过,并由美国律师协会的代表协助—在多处规定中也提及了可促进减少错误的实质指挥诉讼,其被赋予了根本的意义{40}。借此希望大陆法系诉讼文化的代言人—在刚刚启动世代更迭之后—以饱满的自信针对有时笼统而粗放的低毁来捍卫实质指挥诉讼这一对话诉讼模式的优点。
三、当事人对事实的自治与依职权调查证据
(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诉讼文化之间的误解
不同诉讼文化在权衡当事人和法官权限方面一个持久的摩擦点是:大陆法系法官在证据调查方面的强势地位{41}。美国以及诉讼混合文化的代表例如日本{42}特别不能忍受依职权调查证据和法官讯问。在这两个领域,相关的探讨直到今天仍然受到特定的误解的影响,虽然这些误解完全可以被澄清,但却依然继续存在。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主要在于,在trial审理模式基础上的英美法系的诉讼文化并不清楚地区分事实陈述和证据调查,其出发点反而是:当事人通过证据手段以“一次行动”(uno actu)将事实提交给法官。因此,若让法官自己收集证据,就会给这些学者造成误解,因为他们会将此看做是迈向法官纠问和法官事实探知的一个步骤。
(二)依职权调查证据受当事人的拘束
但是,有必要澄清一点:依职权调查证据仅可以涉及当事人此前已经提交的事实,它不得以探知新的事实为目的。对此,rosenberg/schwab/gottwald一书迄今为止非常正确地强调过多次{43}。与《德国民事诉讼法典》未能作出最终的清晰界定—仅从整体意义上才得出了这一重要规则,对此并不存在明确的规定—相比,《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在总则中就明确规定:“为了支持诉讼请求,当事人应提交支持该请求的重要事实{44}。法官不可将未经辩论的事实作为判决的基础……{45}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必须依法证明胜诉所必需的事实{46}。法官有权依职权命令采取法律上适当的任何调查措施{47}。”通过这一清晰的规定,即使英美法系学者也能接受依职权调查证据。以法国民事诉讼法总则为蓝本,这一原则也成为美国法学会和英国共同参与的《跨国民事诉讼程序原则》的内容{48}。此外,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法并非许可任何形式的职权调查,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典》仅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49}许可证人证据,并且在涉及鉴定人证据时受双方当事人共同建议的拘束{50}。不过,在德国民事诉讼中,在依职权和依当事人申请进行证据调查时{51}提交书证义务范围的混乱不清,则属于立法者的重大错误。英美法系诉讼文化对法官通过调查证据的方式探知新事实的厌恶,应当始终成为德国诉讼文化的警示:依职权调查证据不能被贬值为事实纠问,从而造成恰恰为英美法系学者所担心和正确批评的后果—也即纠问式的法官诉讼。
(三)法官讯问证人受当事人的拘束
在英美法系的trial审理中,当事人通过证人和鉴定人陈述事实,并同时对之进行证明。询问证人即意味着当事人对自己的案件进行陈述,交叉询问则是查验对方的陈述。如此一来,事实主张和举证合二为一。若以此为出发点,英美法系的学者肯定会对法官进行讯问产生误会,因为他们将讯问当事人看做是提交事实,因此会再次得出了不为他们所接受的“纠问”的结论。欧洲大陆法系的学者并未真正成功使英美法系的学者从实质上理解法官讯问和律师讯问的不同。在大陆法系诉讼中,讯问证人的内容并非由法官决定,而是由双方当事人通过其事实陈述以及争辩和不争辩在特定的证明对象上拘束法官{52}。也即,法官自身不能—与英美法系诉讼的律师不同—寻找证明对象,即使其他的当事人陈述对于解决案件而言更加合适,但若当事人自身未依指示提交此陈述。德国诉讼强化了法官受当事人通过陈述所确定的证明对象的拘束,这例如与法国的民事诉讼不同,德国民事诉讼法根本不许可法官在起始就进行个别提问,而是让法官承担令证人就当事人的证明对象进行“相关”说明的职责{53}。只有在进行完此项之后,法官在必要时才可提问并直接或间接许可当事人发问{54}。可见,法律希望借此避免法官通过起初发问对证人操纵的后果,证人应当尽可能不受影响地针对当事人的陈述描述个人的经历。法律所确立的这种法官讯问证人的方式并不会产生将诉讼指挥滥用为干涉当事人的事实自治的危险。在这里,英美法系以及日本法律文化的不信任也应当成为大陆法系和德国法官的警示路标:法官不能违法的以“自由”的阐明人自居。在这里,当事人的代理人因不知情或为了逃避糟糕的气氛而沉默,能够很大程度上对此进行补救。
(四)对方当事人的协助义务
“让法官受当事人的证实性事实陈述的严格拘束”的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也不必担心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对方当事人会承担过于广泛的阐明义务(aufklarungspflicht) {55},因为负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作出的可能的证实性事实陈述已对诉讼资料的收集作出了限定,这也就排除了摸索证据(fishing-expeditions)的适用。曾经并且依然与“任何人无须自证其罪”(nemo tenetur edere contra se或nemo cogitur agere contra se)相联系的德国式恐惧{56},早已变得毫无道理,因为法官知道他受当事人陈述的拘束,并且若当事人未对正当事实作出合情合理的证实就不考虑开启阐明程序{57}。卡尔·海因茨·施瓦布在罗森贝克教科书中否定了普遍的协助义务,但他也—正如一个诉讼法学家始终所保持的平衡思考一样—赞同对特定的案件类型采用类似的协助义务{58}。gottwald在续写此书时调整了这一立场,但是他只是从现行法(de legelata)角度反对协助义务的普遍化{59},从立法论(de lege ferenda){60}的角度他却赞同这样做。
四、当事人诉讼与民事司法的私人化
引人注目的是,在诸如美国这样克制法官实质指挥诉讼的诉讼文化中,法院外强制调解和私人仲裁的观念,在过去20年以爆炸式的速度弥漫{61}。原本美国的诉讼法学者将判决程序的无效率看作“美国的优点”,因为它激发了当事人在审前程序通过和解进行自我调整的热情{62} 。不过,过去一些年调解和仲裁浪潮的发展,也可解释为审前程序诉讼和解机制的无效,因为和解需要中立的第三人的促进,而典型的美国法官不这样做,并且甚至也不能这样做。在对话诉讼意义上对诉讼实施实质指挥诉,在现代德国的诉讼中构成了法官卓有成效进行调解的基石,不过,这始终是以法律为导向的调解{63}。很奇特的是,英美法系的诉讼文化一方面在诉讼程序中十分珍视法官的中立地位和当事人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却在诉讼外(且绝大多数是)的强制调解中如此少地保障了调解人的中立地位,它经常因“预备会议”(caucusing)使“原则性谈判”(getting to yes)失去了“兼听则明”(audiatur et altera pars)的可能{64}。对当事人自我发现的拟制,掩盖了在美国并未被赋予法官资格的调解员的职能,尽管与调解员不同对法官存在防止恣意或机会主义行动的规定。德国诉讼中的法官调解至少从质量上看是令人可以接受的、低廉的、经济的,单纯从数量上看也是卓有成效的。毋庸置疑,只有精通以对话形式对诉讼实施指挥的法官才可成功进行调解。不过,将调解法官和裁判法官的角色分离的建议,从而构建出配备了仅担当调解职责的调解法官的“双重法庭”,尽管在实践试验中获得成功,但对此仍然存在争议。尽管如此,人们应当对之进一步进行探讨{65}。人们不应当通过引人广泛蔓延而且归根到底毫无秩序的“原则性谈判”程序,而将现代德国对话民事诉讼的成果破坏殆尽。这种调解程序对于无成效的诉讼文化显得更加适当。实际上,富有长期的司法照管传统和法官和解努力的法律文化{66},在全球关于调解的大讨论中应当可以比对抗主义的诉讼文化带来更多的经验,因为对抗主义的法律文化刚刚才开始发现主动的中立的第三人这一要素,并且伴随着这一青春期的迷恋似乎自此忘记了一些通行有效的规律。人们必须更加清楚地看待和评价美国大量的由非法官进行的“法院附设”强制调解,以便对德国程序中的法官调解持有比目前意见更宽容的评判。它也与现代德国诉讼的方向相吻合。
结语
最后应当强调,诉讼法比较研究不应当被理解为是一种寻找“一劳永逸对当事人和法官责任进行最佳分配”的“最好”程序的发现过程。世间并不存在“最好”的民事诉讼,只存在针对特定的社会结构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能够实现最佳效果的程序。但是,其他诉讼文化的对立思想,可以防止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正是在这一点上,尽管存在太多的不同点,美国的当事人诉讼仍然可以为德国的诉讼法学者和法官带来启示。公正尺度的意义是法官的美德和诉讼的美德,维护这种美德是卡尔·海因茨·施瓦布一直关注的命题,他准确地把握到:极端的解决办法更倾向于排挤公正,而非促进公正。
注释:
{1}本题目由“庆祝卡尔·海因茨·施瓦布教授九十诞辰学术交流会”的组织者为作者设定。作者感谢组织者的邀请,以能向卡尔·海因茨·施瓦布教授表示敬意为幸。
{2}相关文章摘要如下:lent, wahrheits-und aufklarungspflichtimzivilprozess, 1942; bernhardt, die aufklarung des sachverhaltsimzivilprozess, festgabe leo rosenberg, 1949,s. 9 ff.;f. baur, die vorbereitung der mundlichenverhandlungimzivilprozess, zzp 66(1953),209ff.;kuchinke, die vorbereitenderichterlichesachaufklarung(hinweispflicht)imzivil-und verwaltungsprozeβ,jus 1967,295;rimmelspacher, die prufung von amtswegenimzivilprozeβ, 1968,s. 23 ff.;bruggemann, judexstatutor und judex investigator, 1968,s. 125 ff.;w.henckel, prozessrecht und materiellesrecht, 1970. s. 125 ff.,144 ff.;wassermann, der soziale zivilprozeβ,1978,s.68 ff.;starner, die richterliche aufklarung im zivilprozeβ.1982; peters, richterliche hinweispflichten und beweisinitiativenim zivilprozeβ,1983;vollkommer, die stellung des anwalts im zivilprozeβ,1984,s. 50 ff.;sturner/stadler, aktiverolle des richters, in: gilles anwaltsberuf und richterberuf in der heutigen gesellschaft, 1991,s. 173 ff.;m. wolf,zur aufklarungs-und hinweispflichtgem. § § 278 abs. 3,139 zpo, zzp 103(1990),791;e. schmidt, zivilgerich-tliche prozessforderung, festschrift egon schneider, 1997,s. 193 ff.;spickhoff, richterliche aufklarungspflicht und materielles recht, 1999;piekenbrock, umfang und bedeutung der richterlichen hinweispflicht, njw 1999,1360 ff.;prittting, richterliche hinweispflichten im zivilprozeβ, festschrift 150jahrigesjubilaum areios pagos, bd. iv, 2007,s.355 ff.;schumann, die absolute pflicht zum richterlichen hinweis(§ 139 abs. 2 zpo),festschrift d. leipold, 2009,s. 175 ff.;关于历史回顾,参见damrau, die entwicklung einzelner prozessmaximen seit der reichszivilprozeβordnungvon 1877,1975,s. 119 ff.,228 ff,291 ff.,375 ff.,408 ff.,489 ff。
{3}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的相关文章例如有:jack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 justice, 1987. s. 5 ff.,9ff.;andrews, a new civil procedural code for england:party control-going, going, gone, zzpint 3(1999),4 ff.;dens.,english civil procedure, 2003,ch. 13, s. 333 ff.;guinchard/ferrand. procodurecivile, 28. aufl. 2006,rn. 666ff.,5.584 ff.;jacques normand,le rolerespectif des parties et du jugedans les principes de prodedureciviletransnationale,in: ferrand(ed.),la prodedurecivilemondialemodelisee, 2004,s. 103 ff.;cadiet, droitjudiciaireprive, 3. aufl.2000,5.470 ff.;solus/perrot,droitjudiciaireprive , bd. 3,1991,s. 76 ff.;cappelletti,le pouvoir des juges, 1990;pisani, dirittoprocessualecivile, 4. aufl. 2002, s. 204ff.;montero aroca/gomez colomer/montbn redondo/barona silvar, derechojurisdiccional, bd. i, 10. aufl. 2000,kap. 19,s. 328 ff.,334ff.;j. resnik, process of the law,2004,s. 123 ff.,131 ff.;brazil and shapiro, discovery and the adversary process, in: hazard/vetter, perspectives on civil procedure, 1987,s. 123 ff.;murray, civil justice reform in america, zzpint 3(1999),3 ff.;marcus, malaise of the judicial super power, in: zuckerman, civil justice in crisis, 1999, s. 77 ff.,101 ff.;chase, law, culture, and ritual:disputing systems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 2005,s. 62ff.;langbein, the german advantage in civil procedure,52 uni. chi. l. rev. 823ff.(1985)。
{4}对此参见rosenberg/schwab, zivilprozessrecht, 14. aufl. 1986, § 78 14;类似观点参见schwab/gottwald,verfassung und ziviprozess, in: habscheid, effektiverrechtsschutz und verfassungsmapigeordnung, 1983,s. 1 ff.,69。
{5}使用此字眼刻画大陆法系诉讼的英美法系代表人物特别是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tice,1987, s. 5 ff.,7ff.,他所使用的若干批评用语广为流传。
{6}对此参见sturner, the priciples of transnational civil procedure. an introduction their basic concepts,rahelsz 69(2005),201 ff.,223 ff. mnw.;ders.,procedure civile et culture juridiqu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compare 2004, 798 ff.,802 ff以及quelqueremarquessurl’ imageactuelle de la procedurefrancaise, in: cadiet/canivet, de la commemoration d’ un code a i’ autre: 200 ans de procedurecivile en france, 2006, s. 329 ff。
{7}参见guinchard/ferrand, procedurecivile, rn.948 ff.,962 ff.,5.773 ff.,781 ff。
{8}参见redenti/vellani, lineamenti di dirittoprocessualecivile, 2005,nr. 45 ff.,s. 121 ff。
{9}参见《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第183条第三款:ilguidicerichiedealleparti, sulla base deifattiallegati, ichiarimenti necessary……
{10}对此参见weber, die verdrangung des hauptsacheverfahrensdurch den einstweiligenrechtssschutz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1993,s. 44ff.,100 ff.;mossier, beschleunigterrechtsschutzfiirzahlungsglaubiger in europa,2004;也参见piekenbrock, der italienischezivilprozessimeuropaischenumfeld, 1995,s. 94ff.
{11}对加快程序之界限的评析,参见schwab/gottwald, verfassung und zivilprozess, in: habscheid, effek-tiverrechtsschutz und verfassungsmaβigeordnung, 1983,s. 1 ff.,63ff.,65/66.
{12}对此也参见《欧洲小额程序法令(eugfvo)》第2条第一款、第5条第一款、第8条和第9条。
{13}对英国旧程序的概况进行了很好描述的文献,参见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justice, 1987,特别是页29ff. ,68ff.,148ff;关于美国程序的概况参见von mehren/murray,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2. aufl.
2007, ch.6, s. 162 ff。
{14}关于竞争领域的案件参见bell atlantic v. twombly, 550 us 544 (2007);普适化案件参见ashcroftv.iqbal, 129 s. ct. 1937 (2009)。
{15}对此参见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7. aufl. 2010, § § 94 ff.,s. 516 ff。
{16}对此参见esplugues-motal/barona-vilar, civil justice in spain, 2010, s. 16 ff。
{17}关于新英国民事诉讼特别是多轨诉讼,参见zuckerman, civil procedure, rn. 11.52 ff.,s. 435ff。
{18}详见sturner, rabelsz 69 (2005),201 ff.,223 f。
{19}最新一版的教科书仍持此意见,参见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7. aufl. 2010,§§81 i, s.426。
{20}对此参见《拉丁美洲现代法典》第297条及其以下条款、第300条、301条、303条以及barbosa moreira, zzpint 3(1998),437 ff。
{21}参见ali/unidroit, principles of transnational civil procedure, 2006;sturner, rabdsz 69 (2005),201 ff.;德语文本参见schulze/zimmermann(hrsg.),europoischesprivatrecht, basistexte, ⅲ. 60。
{22}参见the faces of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1986。特别是17页及其以下页码。
{23}law, culture and ritual. disputing systems incross-cultural context, 2005,特别是47 ff. , 67 ff。
{24}1793年的《普鲁士王国法院总则(ago)》甚至以职权探知原则为出发点;ago einl. § § 4 ff.,34;关于19世纪普鲁士诉讼的后续发展和德国其他王国的发展,参见bomsdorf, prozessmaximenund rechtswirklichkeit,1971,s. 193~241。
{25}奥地利诉讼遵循一种消弱的职权探知主义或者大大增强了职权探知因素的辩论主义:《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典》第178条、第182条和第183条;对此详见rechberger/simotta, zivilprozessrecht, 5. aufl. 2000, 269 ff.,s. 175 ff.;fasching, zivilprozessrecht, 2. aufl. 1990, rn. 652 f.;s. 344f.;ders, in: fasching, zivilprozessgesetze.kommentar, bd. 1,2. aufl. 2000,einl. rn. 102; bd. 2,2. aufl. 2002,einl. rn. 12 ff.,16 ff。
{26}特别参见197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条;详见stiirner, die richterlicher aufklarung,1982, rn.7,s. 11 f。
{27}详见sturner, procedural law and legal cultures/prozessrecht und rechtskulturen, 2003年在墨西哥城全球诉讼法大会上的开幕词,德语和英语文本见gilles/pfefffer, prozessrecht und rechtskulturen, s. 9 ff.;法语文本“civile et culturejuridique”,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e, 2004,797 ff。
{28}详见andrews, zzpint 3(1999),4 ff。
{29}深入探讨参见wolfgang reinhard, lebensformen europas. eine historische kulturanthropologie, 2004,特别是页301 f.,426 ff.,441 ff.;针对德国的情况参见starner, markt und wettbewerb uber alles?, 2007, s. 48 ff。
{30}这一概念主要出现在法语文献中:jeuland, droit processuel, 2007, nr. 50, s. 67 f。
{31}参见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 § 82 rn. 14, 15 mnw;倾向性更强的观点参见stiirner, richterliche aufklarung, rn. 38,82 ff.,s. 62ff。
{32}参见rosenberglschwab, zivilprozessrecht, 14. aufl. 1986, § 78 i 4;此前就已持此意见的rosenberg,zivilprozeβrecht, 1. aufl. 1927, § 62 i;关于此概念的历史和其与协同主义的关系,详见greger, kooperation als prozessmaxime, in: gottwald u. a.,dogmatische grundfragen des zivilprozesses im geeinten europa(卡尔·海因茨·施瓦布八十大寿的祝贺文集),2000, s.77 ff.,mnw。
{33}对“工作共同体”的诠释,特别要与“协同”的思想区分开来(wassermann最早提出了协同主义的概念,参见其著作der soziale zivilprozeβ,1978, s.109),后者倾向于消弱原本清楚的责任分工,因此受到了学者的批评,参见stein/jonas/leipold, zpo, bd. 3,22. aufl. 2005, vor § 128 rn. 150。
{34}《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6条的内容为:“任何情况下,法官必须监督对抗原则的遵守,他自己也必须遵守对抗原则。仅当当事人有机会以对抗的方式对其进行讨论时,法官才可以将当事人提供或依赖于当事人的理由、说明和文书作为裁判基础。他不得将其裁判建立在他依职权收集而未事先令当事人发表意见的法律观点之上”。
{35}关于《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总则的清晰用词,参见sturner, in: cadiet/canivet, commemoration, s.329 ff.,337。
{36}即便是英国现代的诉讼,其法院管理也更倾向于从高权法官的诉讼指挥角度出发,而并非以法院和当事人之间的对话为出发点;对此参见zuckerman, civil procedure, 2003, ch. 10, s. 350 ff. , 359:“《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在两个重要的方面有别于旧制度,其一,法院在决定程序的性质和时间方面扮演了更突出的角色……第二个革新……包含在首要目标中。通常而言,该目标使当事人的自由受制于一个普遍的适当性标准……这也即是说,为了确保调查(expedition),法院必须对其他自由进行限制……”。
{37} langbein 52 u. chi. l. rev. 823 ff.,826 ff.,832。
{38}《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诉前笔录(pre-action protocols),并实际上对所有重要的诉讼活动都规定了表格,对此详见plant/rose (ed.),civil procedure rules. 1999, s. 895 ff.,927 ff。
{39}简明扼要的概述参见langbein, the influence of the german emigres on american law: the curious case of civil and criminal procedure, in: lutter/stiefel/hoeflich, der einfluβdeutscheremigranten auf die rechtsentwicklung in den usa und in deutschland, 1993,s.321 ff.,328 ff.,329。
{40}对此特别参见《跨国民事诉讼程序原则》(禁止单方交流);3.1和3.1.2; 11.1, 11.2和11.3.2; 142(“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法院应与各方当事人商讨对诉讼进行管理”);15.1.2; 22.2(“当法院给予各方当事人答辩的机会时,可以……”);对《跨国民事诉讼程序原则》规定的法官角色进行总结的,参见stiirner, rabelsz69 (2005) , 201 ff. , 228:“《跨国民事诉讼程序原则》中规定的积极合作型的法官是完全民主式的角色,偶尔带有调解的色彩。法院指挥诉讼进程的职责不应被视为法官职务带有等级色彩的理由”。
{41}中肯意见参见chase, law, culture and ritual, 2005, s. 62 ff.,63, 65。
{42}日本在确定法院和律师在证据调查方面的角色分工问题上借鉴了美国的因素,对此详见taniguchi,in: chase u. a.,civil litigation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 2007,s.35 ff。
{43}参见rosenberg/schwab/c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7. aufl. 2010, § 77 rn. 5, 7, 12,22; § 78 rn.24。
{44}参见《法国民事诉讼法典(c.p.c.)》第6条。
{45}同上,第7条第1款。
{46}同上,第9条。
{47}同上,第10条。
{48}参见《跨国民事诉讼程序原则》11.3, 22;对此详见sttirner, rabelsz 69 ( 2005) , 201 ff.,226 ff.,228 f。
{49}依照《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73条第二款第4项,虽然依职权传唤证人不需当事人事先提起正式的证据申请,但当事人必须为了证明目的援引过该证人;对此详见stein/jonas/leipold, zpo,
bd. 4, 22. aufl.2008,§ 273 rn.29 ff。
{50}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73条第2款第4项;第144条第1款第1句、第404条第1款和第4款。
{51}对此参见bgh njw 2007, 2989, 2991 f.,该判决试图对凌乱的局面进行协调。不过,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拒绝将第142条规定的提交命令缩减到第422条的范围(但不同意见参见stein/jonas/leipold, zpo,bd. 4, 22. aufl. 2005, § 142 rn. 20 ff.;不过,联邦最高法院已这样做,对此详见sturner, festgabe vollkommer,2006, s.201 ff。)。因此,针对这一相互矛盾并且缺乏统一构想的凌乱规定提出的批评也就显得非常有道理。
{52}例如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38条第1至4款,第288条第一款、第358条以下、第359条、第373条、第377条第二款第2项;《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7条、第9条、第10条、第143条。
{53}对此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396条第一款。但司法实践常常未充分注意该条规定。《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08条以下以及第213条的规定赋予了法官明显更多的衡量空间(倾听或讯问)。
{54}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396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397条。
{55}关于此基本问题详见sturner, die aufklarungspflicht der parteien des zivilprozesses, 1976, s. 106 ff.,112ff.;ders, parteipflichten bei der sachverhaltsaufklarung im zivilprozeβ,zzp 98(1985),237 ff.;ders.,rabelsz 69(2005),201 ff.,232 ff. m. w. nw。
{56}此项原则总归是充满争议性。但在涉及不同国家间的诉讼法比较问题时,欧洲境内的法律发展已不再适用此项原则(sttirner, rabelsz 69[2005],201 ff.,234 f. m. nw.)。不仅如此,此原则也与欧洲最高法院的判例不符(1993年11月10日,c - 60/92, otto v. postbank)《跨国民事诉讼程序原则》也明确拒绝采用此项富有争议的原则:“……证据可能对当事人不利……不构成对披露提出异议的理由…”(16.2 [2])。
{57}与过去十年间美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相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新近作成的判例(bell atlantic v.twombly, 50 us 544 [2007],以及ashcroft v. iqbal, 129 s. ct. 1937 [2009])更加突出地强调了这一基本问题。
{58}参见rosenberg/schwab, zivilprozessrecht, 14. aufl. 1986, § 118vi; sturner, zzp 104(1991),208 ff.,212 f. m. nw。
{59}参见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7. aufl. 2010, § 109 rn. 8 ff.,s. 611;具体细节参见§ 110 rn. 15, § 112 rn. 24, § 115 rn. 41, 47 f.;§ 119 rn.35, 43。
{60}参见gottwald, gutachten 61. djt 1996, s. a 15 ff。与此相反,教科书看起来更倾向于避免在法律政策上作出清楚的表态。
{61}相关文献择要如下:murray, die flucht aus der ziviljustiz, zzpint 11 (2006),295 ff.;resnik, contracting civil procedure, in: carrington/] ones, law and class in america, 2006, s. 60 ff.;更倾向于中立意见的hay, zur konzensualen streitbeendigung in zivil-und handelssachen in den usa, in: breidenbach u. a.(hg.),konsensuale streitbeilegung, 2001,s. 101 ff.,118。
{62}参见gross/syverud, don’t try: civil jury verdicts in a system geared to settlement, 44 u. c. l. a. l. rev.1(1996);james/hazard/leubsdorf, civil procedure, 5. aufl. 2001,§ 6.7,s. 381 ff.;murray/sttirner, german civil justice, 2004, s. 578。
{63}详见m. wolf, normative aspekterichterlichervergleichsttitigkeit, zzp 89(1976),260 ff.;sttirner, grund-fragenrichterlicherstreitsehlichtung. driz 1976, 202 ff.;ders.,die rechtsschutzqualitat des vergleichs und die regelung des § 279 zpo, in: w. gottwald u. a.,der vergleichimzivilprozeβ,1983,s. 147 ff.;ders.,la risoluzionealtemati-vadellecontroversie in germania, in: varano (ed.),l’ altra giustizia, 2007,s. 668 ff. m. nw。
{64}关于调解的发展详见goldberg/sander/frank/rogers/cole, dispute resolution, 4. aufl. 2003;关于调解的清晰概述参见von bargen, gerichtsinterne mediation, 2008, s. 13 ff.;hess, 67. djt 2008, s. f 15 ff。
{65}中肯意见参见hess, gutachten 67. djt, s. f 128 f.;详见von bargen, gerichtsinteme mediation, passim,特别是页145以下。
{66}对此参见sturner, festschrfft leipold, 2009,s. 835 ff.;ders.,gedachtnisschrfft manfred wolf, 2010,imerscheinen;英语文本见murray/sturner, the civil law notary-neutral lawyer for the situation, 2010, chapter 2。
出处:《清华法学》2011年第2期